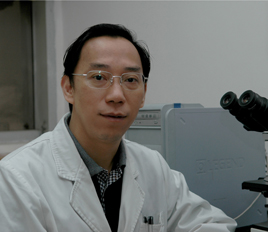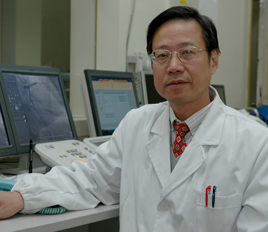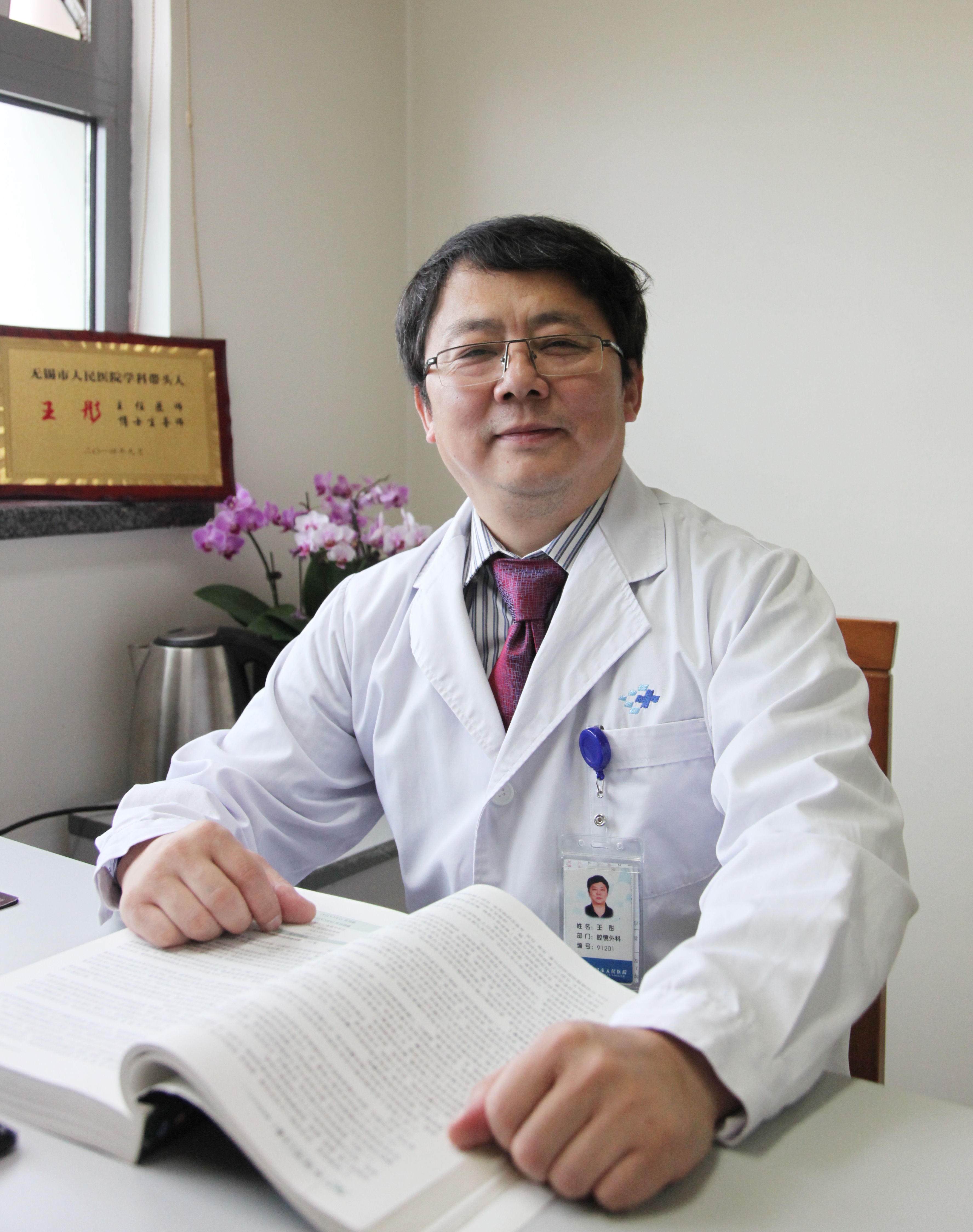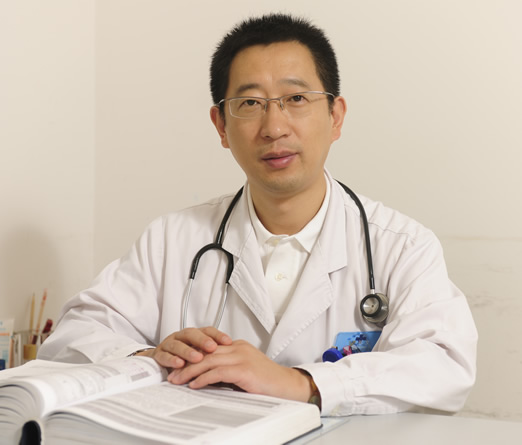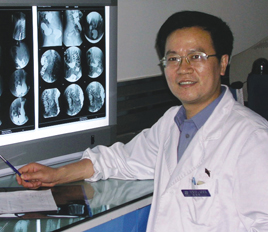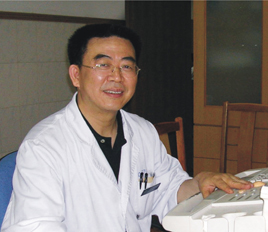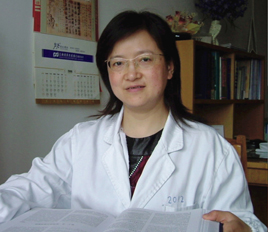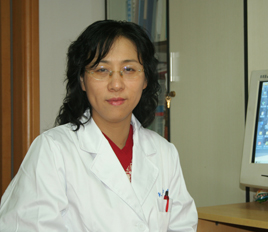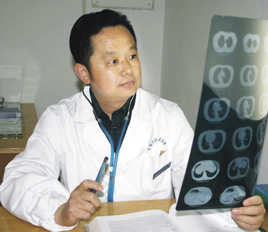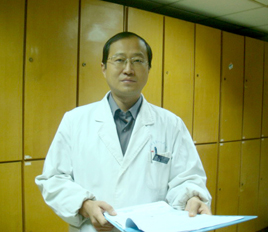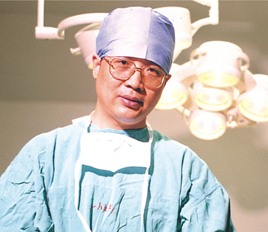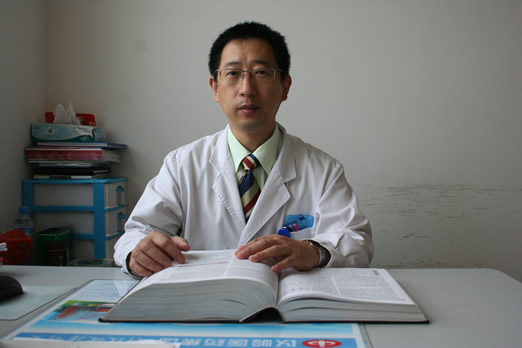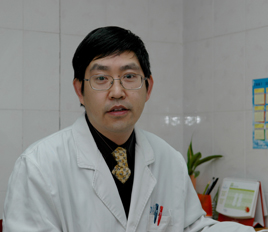一
七十年代初,一个炎热的夏天,灼热的空气令人呼吸都感到困难。养母牵着我的手,一路坐了火车又赶汽车,匆匆地到了上海肿瘤医院,当养母推开病房门的时候,映在我眼前的是一间很大的病房,只有一张病床,那上面躺着父亲。
我走到父亲床边,父亲原本白晰清秀的脸,现在让我看了害怕起来,腊黄腊黄的,面颊骨把脸上仅剩的一点皮层顶得嶙峋凸起。
母亲在床边伺候,一边劝父亲不要多说话,一边给父亲接上氧气,大概是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了,看到我和养母,想挣扎着坐起来,却没有力气,身子如同瘫软了一样,脸上微微的一笑,对养母招呼了一声“姐姐!”
父亲把头从枕头上转过来,毫无表情地看着我,手却抓住了我的手臂,抓得很紧…我突然觉得父亲离我是那么遥远,他原本是那么高大,脸上永远都带着让人亲近的笑容,是病魔摧残了他的躯体,把他硬生生的拖向黑暗之中。
养母要带我走了,这时候父亲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听话,好好学习。”
这句话成了父亲给我的最后嘱咐。
二
父亲死了,那年他38岁。临死前他向母亲交待了两件事:第一件要把他的两大箱医书保存好。第二件是一定要把儿子扶养成人。这两件事,今天都做到了。父亲交付的这两件事,是父亲想做又没有做好的事情,一方面说明了他对医学的深爱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家庭对孩子的愧疚。
我们如何才能了解那个年代父亲的内心?如何理解建国初期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悲痛和喜悦?
父亲1955年山东医科大学毕业,到北大荒的军垦医院做了10多年的内科医生。
那是1957年的冬天,母亲怀着父亲的第一个孩子,乘上北去的列车,去北大荒探亲,母亲在火车上颠簸了三天三夜,内心充满着对丈夫的向往,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天伦之乐。
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,母亲挺着肚子,下到站台上,说是火车站,其实仅仅是一块木板钉起来的站名显示牌,所谓站台就是一块用石子铺成的开阔地。火车站人来车往,马嘶人叫,热闹非凡。父亲借了一辆马车到车站接站,母亲几乎认不出面前的父亲了,身上披着羊皮,头上戴着翻毛皮帽,活像一个东北山里的大汉。两个人见面以后的兴奋刚过,母亲就靠在大车的车邦边,伴着马铃的叮当声睡着了。到了父亲宿舍,饥饿和劳累的母亲满以为会有一顿丰盛又热气腾腾的饭菜在等待她,可是父亲只端来了一碗窝窝头面糊汤,母亲的眼泪叭嗒叭嗒落到了碗里。她怎么都没有想到,北大荒的生活是如此的艰苦,父亲在信中从来没有向母亲作过细致的描述,她对父亲狠狠的说,要是知道如此,就不会来了。父亲看到母亲的眼泪,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,不知是内疚还是遗憾。
军垦医院正在初建,病房是土坯垒起来的,虽然简陋,但一排排的房子整齐地排列在黑土地上,显得很有规模,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医学院校来的专家和热血青年,他们立志建设国家富饶边疆,因此医院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,父亲整天呆在病房,或者下到工地、农场巡回医疗,母亲去探亲半个月时间,有父亲伴在身边的时间只有3个晚上,母亲是气鼓鼓的回来的。现在母亲每当说起这段往事,总觉得对不起父亲,感到自己不应该给父亲带去眼泪和任性。
三
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北大荒又地处反击苏修霸权的前线,在一次边疆地区政治清查中,父亲被要求退出军垦系统,父亲只好回到家乡的县医院做医生,不久文革开始了,父亲又被下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,他少年时就离开的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。
那时候放寒暑假,我才有机会跟着哥哥弟弟们到父亲那里的县城去。我印象当中,父亲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才回到县城的家。就是星期天,父亲也很少有空闲,几乎每次回来后,都会被县医院的同事叫去会诊病人。有一次隔壁的金医生来家里找父亲讨论病例,两个人争论起来,父亲以“希氏内科学”里的典型作为依据。金医生让我把这本书搬出来。父亲说在第几章里可以找到,金医生翻到那里,果真是的,这令金医生赞叹不已。我至今都为父亲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而惊奇,足足有10公分厚,A4纸那么大的一本书,竟然能把里面的内容记得滚瓜烂熟,几乎可以背下来,而且那是一本英文版的。
母亲后来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书交我保存,其中就有“希氏内科学”英文原版本,里面还夹杂着好多父亲亲手写的记录纸片。
四
我参加工作那年,去探望母亲,老人家嘱我去看看父亲的坟,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,我没有去看过他。弟弟陪着我,坐了半天时间的船。
在父亲坟前,我流了泪。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流泪。父亲给我的印象很陌生。一直到他故去,我见到他,就是可数的那么几次,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
弟弟还小,在上中学。他把我带到这个地方,一点也看不出他的陌生,中午刚到,弟弟告诉我说:“在这里的农民家里,我们坐下来就能吃饭。”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但当我和弟弟走进村子,“钱医生儿子来啦!”随着一个农民的一声招呼,几乎是突然之间,一下子冒出来好多农民,他们从家里纷纷跑出来,把弟弟和我围在了中间。
曾经跟随父亲工作的女赤脚医生把我们拉进家门。在乡亲们的热情招呼下,我美美的吃了一顿饭,同时听着他们不停地讲述父亲生前故事。
父亲做乡村医生有4年时间,那个年代,乡村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,就是有很大学问的人了,虽然父亲身上背负着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名,但在纯朴的农民眼中,父亲是了不起的人,也因此,父亲没日没夜地看病救人。
女赤脚医生说了这么一件事。一个大冬天,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去,一个产妇在家生产时遇到难产,父亲被叫去抢救,跟着来求救的农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,到产妇家的时候天都黑了。那时候,没有什么交通工具,如果走水路还好一些,生产队里有船接送,走陆路的话,只有靠两条腿了。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,一个内科医生怎么会去做助产士的工作呢?是啊!那个年代,农村里有一个医生很不容易,农民们不会区分医生的专业,只要有人病了,都要找你,所以乡村医生样样都要会一手。
到了农家,父亲到产妇床边一看,胎儿的一条腿已经露出来了,这种胎位是没法顺产的,时间长了,大人和孩子都很危险。父亲把孩子小腿退回产妇子宫,用手法使孩子在产妇体内旋转了180度,终于使孩子顺利产出,那个产妇的男人就给父亲磕头。
忙完了产妇,已经是下半夜了,在往回走的路上,父亲在荒地里迷了路,转了很久也走不出来,旷野里还积有厚厚的雪,踩在脚下又滑又泞,没有走稳,一下子跌到了水沟里,浑身上下湿漉漉的,父亲饥寒交迫,一直在野地里转到东方泛白才找到回家的路。父亲生了一场病,发高烧,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。
在农村当乡村医生,没有坐等病人上门的看病方式,农民有需要找医生,都是直接到家里,而且往往是要医生出诊。那时候,医生不会讲价钱,不会讲条件,背上药箱就出门,父亲的名声在十里八乡可响了。
五
父母育有四个儿子,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,作为医务人员出身的父母,他们的前半生历经了颠沛流离,不可能分出精力照顾孩子。母亲的姐姐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照顾我们兄弟的担子,我们兄弟四人对自己幼年时期的父母也许印象不深,但对这位母亲的姐姐却特别亲近,在我们蹒跚学走路那些日子里,都是在她跟前绕膝,我们兄弟也都是异口同声地叫她妈妈。这位妈妈因我们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,很晚才成家。我从小跟随她生活,她就是我在前面文中提到的“养母”。
我的哥哥后来随了舅舅在城市里生活,大弟弟和小弟弟在我“养母”这里长大后才回到母亲身边,这时候父亲已经故去了。父亲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力亲手扶养自己的孩子,一直因此而耿耿于怀,我的大哥寄养在舅舅家,父亲不情愿,把哥哥带回乡下,父亲由于忙,把哥哥整天关在小屋里,锅灶里放了一天吃的饭。一次哥哥爬出小屋,走失了两天。父亲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,只好又把哥哥送回到舅舅和舅母那里。
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,也是父母甘苦的见证。恋人、夫妻、乃至一个家庭,沐浴在爱河里的幸福,一定是建立在对未来憧憬的基础上,一个对未来没有美好向往的内心是不会让幸福驻足的。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,天各一方,可从来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,正是因为有了对未来的期待,使我们大人和孩子或聚或散,心却始终凝聚在一起。
六
关于父亲的故乡、故居和他的祖辈,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忌讳的话题。地主前面再加上恶霸两字,就像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父亲的身上,直到他走完生命的全程,他都没有敢于抬起头来看人、看社会。
解放战争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,苏北地区都是国民党的天下,即使是在日本侵华的铁蹄下,也少有踏上这块土地,这使得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政权,横行乡里。抗日战争结束后,新四军的势力在苏北地区迅速扩展,那些依附于国民党的土豪劣绅感到了威胁,建立起保安团之类的地主武装,企图抗击新四军的渗透。父亲的祖父置枪支拉队伍,庄园四周挖起了护庄河道,建起了吊桥,成为当地的恶霸。然而这股地方恶势力在汹涌澎湃的解放战争洪流中,如残破土墙,顷刻间土崩瓦解。可怜了还幼小的父亲,为躲避灾难,只身一人,背起行囊,到江南投靠家里的挚友。
那是一位开药铺的中医老先生。在这位老先生的悉心关照下,父亲完成了初中、高中的学业,在建国初年考上了大学。
父亲少年时期聪明刻苦,沉静稳重,人也长得俊气,为街坊四邻们所喜欢。这时候隔壁一家开米铺的二姑娘活泼伶俐,虽小父亲五岁,却总喜欢拉着这位哥哥玩耍,时间久了,情窦孕育,私结情缘,后来这位二姑娘就做了我的母亲。刚解放,当父亲考上医科大学时,母亲也从学校报名参干,一天,街坊急匆匆回来告知母亲家的老太爷,说是二姑娘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正在大街上参加游行呢。母亲瞒着家里参加部队,如同家里的屋顶遭遇雷击,可急坏了一大家子人,那时候家里人胆小怕事,不知道时局好坏,就想着守着一点家业过安稳的日子。家人紧急商议,把母亲从学校连哄带骗拉回家,关在了阁楼上,母亲哭天喊地,绝食抗争都没有人答应。最后,参干的学生们随部队走了,母亲只好死了这条心,这时她提出要考护士学校,家里同意了,不久,母亲被扬州护士学校录取,总算是部分随了母亲的心愿,跟着自己爱恋的人一起从事医疗事业。
令这对充满幻想的年轻人没有想到,他们从此开始了一段艰辛的从医历程,走上了一条许多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。
七
父亲的出身害了他,被清理出军垦系统后,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,躺在病床上的时候,他对照顾他的母亲说过,他最不甘心的就是这一挫折,也许,在他看来,他的宏图大志就此破灭了。离开北大荒之前,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,父亲这样表露过:“一旦离开了医院,我的人生就没有一点意义了,医院和病人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,所以,即使我去家乡当一个乡医,我也要去。我不会去做别的,这点请你理解,……”当父亲回到家乡,虽然还是当医生,但他内心还是不服,总是闷闷不乐。那时候,母亲在苏南一座大城市的一家福利待遇极好的军人医院工作,有姐姐帮着照看孩子,生活相对还是稳定的,现在父亲回到了家乡,家里原本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,这个家何去何从呢?父亲坚决不愿回到母亲这里吃闲饭,母亲也不忍心再让父亲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,在这左右为难之际,是母亲的姐姐起了关键的作用,她毅然在当地嫁人,把父母的几个孩子揽在了自己身边,催促着妹妹回到丈夫身边去。
母亲从城市回到乡村,从条件优越的军人医院来到贫困落后的工作环境,是一个巨大的跨越,这种跨越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。母亲为了父亲,为了这个家,勇敢地跨了出去。
夫妻团聚,那怕再艰苦,也是苦中有甜。平静的县城生活开始了,父亲当医生,母亲当护士长,在那时的县级医院,用现在的话来讲,都是杰出的人才,受到同行们的尊敬,受到民众的信赖。生活虽然简朴,但在当地算作是高工资了,吃穿不愁。没有想到政治风云再度突变,文革的狂风暴雨横扫过来,父亲又从县城下放到乡村,母亲也随后不久下放到乡村。这时候,知识分子的傲气时时折磨着父亲,他一边为农民治病,一边又深感怀才不遇,在一个外表看似热爱农民,热爱乡村的乡村医生的内心,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高等学府和城市大医院里展示自己才干的渴望。我想,正是父亲的这种孤傲与渴望伤害了他自己,催促他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终结。
八
就在我和养母去探望父亲的第二天,父亲村里的农民们匆匆忙忙赶到上海肿瘤医院探望。站在父亲的床边,一个老人从身旁妇女的手里拿过蓝布袋子,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包裹,打开后显出几只深黄色的植物。
老人对父亲说道:“这是灵芝,带给你熬汤喝的。” 老人告诉父亲,乡下的农民有两天没有下地劳动,生产队派全体社员都到荒坡野地里去找灵芝,终于找到了两只,大家凑了一点路费就送来了。
在乡下,农民们把灵芝看作是神草,喝了灵芝汤可以起死回生。农民们期待着灵芝这种神草能救父亲一命,让他病好了再回到乡下去。
父亲活着没能再回到乡村,按照父亲的遗愿,把他葬在了乡村。
 上一篇:假如我是病人(诗歌)
上一篇:假如我是病人(诗歌) 下一篇:光荣啊!五院
下一篇:光荣啊!五院